欢迎访问新医改评论 XYGPL.COM 您是第 3571516 位访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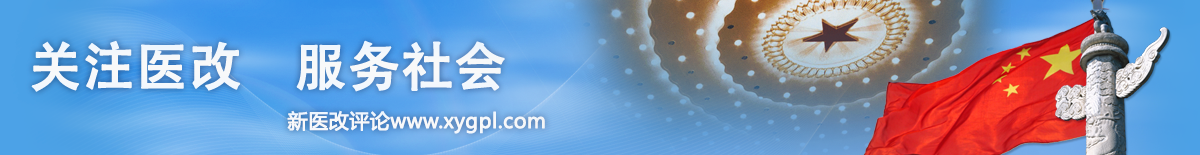
题记: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发院经济学教授刘国恩应新经济学家智库的邀请,做了一个TED式的演讲,探讨如何让人人看得起病。这篇演讲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大生命科学院原院长、首都医科大学原校长饶毅教授发表见解,其点评有肯定,也有值得商榷之处。刘国恩教授针对饶毅教授的点评认真回复。愿此良性的学术研讨、观点争鸣能让更多人关注和思考医改与健康问题。
对刘国恩老师“人人如何能看得起病”的赞同和批评:不能盲目模仿美国
饶 毅
众所周知,解决医疗问题,不仅是全世界人民众望所归,而且迄今没有一个国家拿出了公认切实可行的良方。
一般传说中好一点的办法也有争议。而美国也承认没有好的办法,经常出现较大矛盾。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刘国恩老师,最近有个演讲,题目是“人人如何能看得起病”。
这个题目非常好,我非常赞同。
我和一般读者一样都很关心,以为世界上终于有良方解决这么重大的问题了,抱着高度热情赶紧认真阅读。
刘老师演讲中的四个具体办法,我有赞同、有批评,也有具体建议。要达到刘老师题目的目标今后还有很长的路,“尚需努力”。
刘老师的四个办法:1)医生走出大医院,到社区服务;2)通过预防而减少疾病;3)减少药物费用;4)人工智能增加医疗效率。
以下为具体商榷:
1)走出大医院、发展社区医疗并不能解决医疗费用问题。
刘老师对美国等国私人医生降低费用的观点恐怕不仅不是应该推荐的好办法,而是对基本事实判断有误。
美国的医疗费用奇高,完全不是中国学习的对象。
医院之所以优于私人诊所,是集中和共享仪器设施、医生便于会诊。如果私人诊所也有仪器,因为共享困难,必定价格增加,导致费用增加。那些环境优雅的私人诊所,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病人付费。
私人诊所,如果不能共享仪器设施、难以会诊,医疗质量必定降低。
美国有两类私人医生,一类是在富裕区域的,一类是农村的。前者的价格高于大医院,后者的质量远低于大医院。所以,美国并未拿出办法做到质量高而价格低、没有提供中国可以借鉴的办法。
在医疗方面,质量可以借鉴美国,价格、“人人如何看得起病”完全无法效仿美国,可以总结其经验教训。
中国同样无法从社区医生解决问题。人们纷纷去大医院,是为了医疗质量。社区只能看一般的病,全世界都一样。一般的小病很多病人可能自己熬过去,而严重的都会去大医院是人之常情,不是价格规律(命比钱重要)。
2)通过改变生活方式降低疾病发生。我非常同意刘老师这一观点。特别是我国吸烟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决。如果不吸烟,肺癌就是罕见病。很多人不知道,吸烟不是导致人人患肺癌,但是提高一部分人肺癌发病率。对于这一部分人,吸烟的后果非常严重。人们不应该用自己、自己的家庭做实验,以身试法吸烟试试自己是否属于吸烟导致肺癌的那部分。
3)降低药物费用。美国模式是不断出现新药,一般来说是效果更好,但费用更高。美国各方面都对此怨声载道。特朗普的全部政策中,我唯一赞同的就是降低药物费用。应该不断有新药,但是在提高治疗效果的同时,应该要求费用与以前的药物持平,不增加。这样,医药总体占家庭、社会、国家的支出比例不增加。这才是医疗长期的出路。如果费用越来越高,各国都无法承受。
4)人工智能提高医疗效果。我也赞同并且相信。但是,提高效率不一定降低费用。需要有措施才能在带来疗效的同时降低费用。
引用刘老师一部分内容: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政府办医非常强大的英国,他们的医生基本上都是自由职业者,他们在医学院校的时候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加自己父母亲的资金,自己贷款的资金,好不容易把医学院读完,然后开始去找到一份工作,要还巨额的贷款,大家想想,他们如果都待在公立医院里面,靠着那份固定的薪水要还这笔大的贷款,那是多么大的负担。
但是他们大多数的医生都会在社区去建立自己的诊所,他的工资、灵活程度,他的时间安排就会比在一个固定的医院里要充足得多。
所以他们完成医学院以后,基本上多数的医生都会在社会平台去开自己的诊所去服务大众,从而使得自己做医生的梦想能够体面地得到实现。
以上这一段没有写清楚。如果写清楚,那么按这模式,社区医生收入高于大医院,费用必定来自病人。这与刘老师降低费用的目标是南辕北辙。除非说,“看得起病”变成“就近看得见医生”。
我不赞同高收入的社区医生。增加这类医生不是中国的可行之路,在美国也困难重重。
美国的缺点,在今天很多人都知道,这就是其中一点。我们今天肯定不能不加分析、更不能学习美国的缺点。
答饶毅教授:医改十余年,我们为何仍困在“虹吸”的局里?
刘国恩
饶毅教授好,中秋节快乐!
昨日拜读您对我在"太学"频道关于"人人如何看得起病"发言的评议,受益良多。医改这道世界性难题,能在佳节之际得您如此用心点评,实在是公共讨论的一件幸事,特此致谢。
说来我们讨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如何看待中国"大医院与社区医疗"的复杂关系。这个问题确实头绪很多,三言两语难以说透。不过在我看来,要改革当前以大医院主导资源配置的医疗体系,关键还是要回到2009年医改提出的"分级诊疗"这个方向上来。加强社区医疗、解放医生,这个大方向,我始终坚信不疑。至于我的演讲,因为是即兴发言,难免有表述不周之处,若因此引起听众误解,还望海涵。
您提醒"不能盲目模仿美国",这话说得在理。不过我想补充一句:借鉴他国经验,重在取其所长。我们研究发达国家的医生流动模式,取的是他们"尊重专业价值、畅通人才流动"这个理,具体做法当然要符合中国国情。
从经济学资源配置的角度看,我之所以反复强调"解放医生"和"社会办医",主要是针对当前医疗服务过度集中的中国“特色”问题。大医院的"虹吸效应"确实令人担忧,以下三方面的观察或许能说明问题:
其一,资源配置失衡的问题日益突出。2009到2019这十年间,医院卫生人员增长了96.6%,基层却只增长了32%。在基层调研时,常常看到医疗设备闲置,而大医院却总是人满为患。2022年郑州那起"40名专家集体跳槽"事件就很能说明问题——这不是普通的人才流动,而是典型的"虹吸式挖人"。一个科室的骨干集体离开,导致原医院的诊疗能力大幅下降,患者不得不转向本已拥挤的大医院。研究数据显示,三甲医院比重每增加10%,城乡医生资源配置不均衡就会扩大16%-21%,西部地区这个问题尤其明显。
其二,医疗服务效率的提升遇到瓶颈。新医改推行十余年,分级诊疗的进展如何?让我们看看数据:2011到2021年间,基层诊疗人次从38.1亿增至42.5亿,增长12%;而三级医院则从9亿猛增至22.3亿,增长148%。除非这十年国人的健康状况出现了什么大问题,否则这个数字背后反映的,恐怕是体制上的症结。实地调研发现,三甲医院七成以上的门诊患者,其实都是普通常见病。这些病症完全可以在社区解决,既方便又经济。现在这样的就诊格局,把本该有序的分级诊疗网络打乱了,基层医疗机构渐渐沦为"开药窗口",还谈什么健康守门人?
其三,"虹吸效应"的成本最终要由医保基金来承担。虽然各国都存在过度医疗,但我们面临的是住院与门诊不分的结构性矛盾。有研究显示,这方面的浪费可能占到医保支出的12%-15%,我个人觉得这个数字还可能被低估了。当然,反过来看,这也说明医改的潜力还很大,关键要看劲往哪里使。
说到改革路径,或许见仁见智。但我认为根本还在于"解放"大医院的医生,让他们成为能够自主执业的社会力量。这不是要把医生都赶出去开诊所,而是要让这支专业队伍像活水一样,该汇聚时成深潭,该流动时润四方。现在全国2188个县推行医共体,去年双向转诊达到3656万人次,增长两成,这说明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是需要更多时间和耐心。
我理解您对"社区医生收入推高费用"的担忧。但我们要看到,当前国内基层医生的薪酬水平远低于大医院,全科医生的收入差距尤其明显。关键是要改革"收支两条线"的补偿机制,建立以服务质量为核心的考核体系,让基层医生"留得住、有干劲"。试想,如果数百万中国医生在执业发展、收入待遇、社会保障等方面能够自主选择,"强基层"或许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研究表明,"强基层"不仅能改善居民健康,还能降低医疗费用和个人负担。同时,"解放医生"促进社会办医,有利于形成良性竞争,从而降低整体医疗成本。
说到医疗费用控制,美国的教训确实要引以为戒——他们的医疗开支占到GDP的18%,而我们还在7%上下。但德国通过疾病基金覆盖96%人口,英国实现全民医疗,新加坡用个人账户平衡责任。在这些国家,社区医生大多是自由执业者,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而不都是窝在大医院的"单位人"。这些经验告诉我们,医疗服务效率和医生自由执业并不矛盾,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说到底,医改既要懂天下大势,更要解中国难题。十多年的实践表明,如果不能从制度上破解"虹吸效应",再好的政策都可能流于形式。解放医生、重构资源流动机制,绝不是要照搬西方模式,而是针对中国"集中式医疗"顽疾的对症之药。您我或许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但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的初心是一致的。医改之路任重道远,更需学界同仁如你我之辈秉持理性、共同探索。
盼再交流。
刘国恩
|
|
||||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