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新医改评论 XYGPL.COM 您是第 3529109 位访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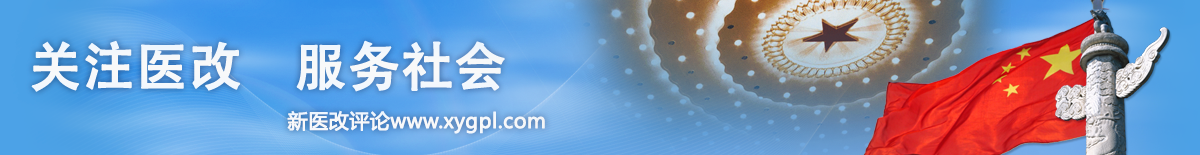
今天我们要来谈北欧的税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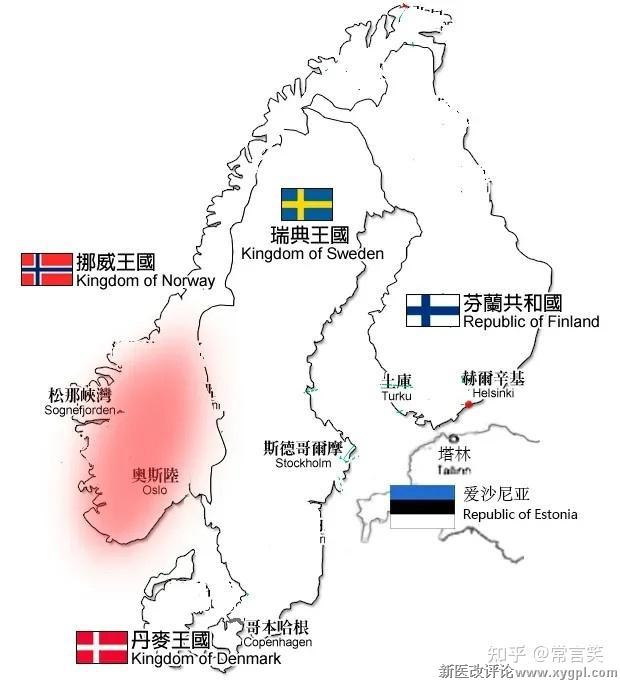
一说到税,你可能觉得,这有啥好聊的?天经地义嘛。咱们中国人从小就被教育,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在西方呢,也有一句名言,叫世界上只有死亡和税收不可避免。
你看,全世界的人好像都默认了,交税,就像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是个自然法则。
尤其是在讨论北欧模式的时候,高税收更是被描绘成一种美德。
它的逻辑是这样的:我们每个人都把一大部分收入贡献出来,汇集到一个公共的池子里,然后国家这位大管家,再用池子里的钱,为我们提供教育、医疗、养老等各种服务。
这不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现代版吗?
听起来,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有集体荣誉感的社会契约。
这个契约论,就是高税收最重要的道德光环。
它把一个冷冰冰的强制行为,包装成了一个温情脉脉的集体选择。
但今天,咱们就要把这个光环给摘下来,看一看它底下到底是什么。
我的老规矩,还是先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假设你住在一个小区里,有个非常热心的邻居,他成立了一个小区互助委员会。他说,为了大家的安全和幸福,我决定,每个月从你们每家每户的工资里,直接划走一半。
然后呢,我用这些钱,雇几个保安,修一下小区的路灯,再办个食堂,大家可以来免费吃饭。
你会有什么反应?
你可能会说:等等,凭什么啊?
谁授权你从我工资里划钱了?
我同意了吗?
我想自己决定请哪个保安公司,不行吗?
我不喜欢你食堂的饭菜,想自己在家做,不行吗?
如果这个邻居回答你:这是为了大家好,是为了小区的集体利益。
你既然住在这个小区,就得遵守这个规矩。这是你的义务。
然后,他还找了几个壮汉,谁要是不交钱,就堵在你家门口。
这时候,你还会觉得他是个热心的好邻居吗?
你大概率会觉得,这不就是黑社会收保护费吗?只不过他说得比较好听而已。
好了,这个小区的故事,你先放一放。
咱们现在用三把手术刀,从三个层次,来解剖一下税收这个东西,特别是北欧那种高到令人咋舌的税收。
这三个层次是:伦理的、经济的、和心理的。
第一个层次:伦理社会契约还是合法抢劫?我们先从根儿上刨。税收,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
我们用第一章讲的那个元规则 —— 还原到人 —— 来分析。
所谓的国家向公民征税,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群叫政府官员的人,依据一部叫法律的文件,强制性地,从另一群叫国民的人那里,拿走他们财产的一部分。
注意这几个关键词:强制性地、拿走财产。
这在伦理学上,就带来一个巨大的挑战。
我们都同意,私有财产是神圣的。我通过劳动赚来的钱,就是我的。你不能抢,他不能偷。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那为什么,当抢劫这个行为的实施者,从张三李四换成一个叫国家的组织时,它就突然变得合法,甚至高尚了呢?
人数多,就是正义吗?
穿上制服,就是合法吗?
打着为了你好的旗号,就可以侵犯你的财产吗?
这就是问题的要害。
契约论的支持者会反驳说:这不是抢劫,这是我们自愿达成的契约。
我们通过选举,授权政府向我们征税,来换取公共服务。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美,但它经不起推敲。
你签过这份社会契约吗?
你出生在这个国家,这份契约就自动生效了。你没有任何机会说不。一个不能拒绝的契约,还能叫契约吗?那叫霸王条款。
你能退出这份契约吗?
你说,我不想享受你的公共服务了,你也别收我的税了,行不行?不行。除非你移民,放弃国籍。
但这就像那个小区的故事里,你不同意交保护费,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房子搬家。这能叫自愿吗?
这个契约的内容是你可以选择的吗?
国家收多少税,怎么花,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个人有发言权吗?你可能会说,我有选票啊。
但在一个几百万人的国家里,你那一张票的实际影响力趋近于零。
最终,你还是得被动接受那个由多数人(或者说,由控制了政府的政治集团)决定的服务套餐。
你无法像在市场上一样,说我只要A服务,不要B服务。你必须全盘接受。
所以,当我们用最严格的逻辑去审视,社会契约这个说法,其实是个美丽的谎言。
它把一个强制性的权力关系,伪装成了一个平等的交易关系。
在北欧这种高税收国家,这个问题就更加尖锐。
当税率高达 50% 、 60% 甚至更高的时候,意味着你一年里,有半年以上的时间,是在为国家这个组织无偿劳动。
你一半的生命时间,其产出成果不属于你自己。
从伦理上讲,这和古代的徭役或者农奴制,在本质上有多大区别呢?
只不过它表现得更文明、更隐蔽,用钱而不是人身来体现。
所以,这是我们对税收的第一个,也是最颠覆性的认知:
抛开那些宏大的叙事,税收,在伦理的根基上,是一种由国家垄断的、合法的、强制性的财产转移。它和自愿贡献是两码事,在性质上是截然相反的。
把这个想明白了,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高税收一定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后果。
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违背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个最根本的原则。
第二个层次:经济一部惩罚成功、扼杀活力的财富粉碎机
好了,就算我们暂时把伦理问题放一边。我们务实一点,只看结果。
支持高税收的人会说:别管它在伦理上怎么说,只要它能带来一个好结果 —— 一个富裕、平等的社会,那它就是好的。
那么,高税收真的能带来好结果吗?
咱们用经济的这把刀,切下去看看。
高税收是一只漏水的桶。
经济学家阿瑟 · 奥肯有个著名的比喻。他说,用税收搞财富再分配,就像用一个漏水的桶,从富人那里舀水,送到穷人那里。
在这个过程中,水一定会漏掉一部分。
漏掉的那部分是什么?
就是我们常说的无谓损失。
这个词有点专业,我给你翻译一下。
它指的是:因为税收的存在,而导致那些本来可以发生,但最终没有发生的、能创造价值的经济活动。
举个例子。
一个软件工程师,他正常上班 8 小时。
下班后,有个朋友想请他做个私活,写个小程序,报价 1 万块。
他盘算了一下,这个活儿得干 50 个小时,平均每小时 200 块。
他觉得还行,挺划算的,准备接。
但这时候,他想起来了,在北欧,他这 1 万块的额外收入,可能要交 70% 的税,也就是 7000 块。
最后到手只有 3000 块。
这么一算,每小时的收入就从 200 块,暴跌到 60 块。
他可能就想:算了,为了这点钱,搭上我 50 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不值当。我还是在家躺着看电视吧。
你看,发生了什么?
这个工程师,没有赚到那 3000 块。
他朋友,没有得到那个想要的小程序。
社会,也损失了一次价值 1 万块的、本来可以被创造出来的服务。
政府呢?它一分钱的税也没收到。
因为它把税率定得太高,导致这个交易本身就流产了。
那个被扼杀掉的、价值1万块的交易,就是漏掉的水,就是无谓损失。它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谁也没得到。
这就是高税收的第一个恶果:它不是简单地把钱从 A 口袋转移到 B 口袋,它是在转移的过程中,把一部分钱直接给粉碎了。
税率越高,这种粉碎效应就越严重。整个社会的经济蛋糕,不是被重新切分了,而是变小了。
高税收是在惩罚社会活力的发动机。
谁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者?
是那些最勤奋的工人、最有才华的专家、和最敢于冒险的企业家。
他们是经济的发动机。
高额的累进所得税(就是收入越高,税率越高的那种),它在干什么?
它在精准地给这些发动机踩刹车。
你工作越努力,收入越高,我从你身上抽走的比例就越大。你承担的风险越大,创业成功了,我拿走的利润也越多。
这传递的是一个什么信号?
干得好,就罚你。
这完全扭曲了正常的激励机制。在一个人人都要为自己负责的社会里,激励是多劳多得。而在高福利社会里,激励变成了多劳多税。
结果是什么?
我们上一章提到的瑞典病。
先是人才外流。
最顶尖的医生、工程师、金融家,他们会选择去税率更低的国家工作,比如瑞士、美国、新加坡。因为他们的才能在那些地方,能换回更多的个人财富。
接着是资本外逃。
企业家们,会把公司总部和利润,想方设法地转移到爱尔兰、开曼群岛这样的避税天堂。这不叫不爱国,这叫理性选择。
资本就像水一样,天生就要往低处流。
你非要筑一个高高的税坝,那水就会绕开你,或者从堤坝的缝隙里渗出去。
最终,你这片土地就会越来越干涸。
我们来看第一个巨人:宜家(IKEA)的创始人,英格瓦·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
坎普拉德可以说是瑞典梦的化身,他从一个农场里卖火柴的小男孩,最终打造了一个全球家居帝国。
但就是这样一位国宝级的企业家,却在1973年,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瑞典。
他去了哪里?先是丹麦,后来是税率更低的瑞士。
他为什么要走?他自己说得非常直白。
在七十年代的瑞典,财富税和遗产税高到什么程度?
高到他根本无法将自己亲手创立的公司,完整地传给自己的孩子。
如果他留在瑞典去世,他的继承人为了缴纳天价遗产税,唯一的选择就是卖掉公司股份,把宜家这个庞大的商业帝国给拆了。
这就像你辛苦种了一棵苹果树,硕果累累。
邻居(国家)说:这树长得真好,等你不在了,你的孩子要想继承这棵树,必须先把一半的树枝砍下来给我。
这合理吗?
坎普拉德的选择,是把整棵树连根拔起,移植到一块更肥沃、更友善的土壤里。
他在瑞士一待就是40年,直到2013年,瑞典废除了财富税和遗产税之后,他才在晚年重返故乡。
这是一个长达40年的无声抗议。
一个国家的税制,硬生生把自己的“国民企业家英雄”逼成了“经济难民”。
你以为这只是个例吗?
我们再看一个:利乐包装(Tetra Pak)的创始人家族,劳辛(Rausing)家族。
今天我们喝的牛奶、果汁,很多都用着利乐的无菌包装。这家公司同样是瑞典工业的骄傲。
但它的掌门人汉斯·劳辛,也在80年代初,做出了和坎普拉德同样的选择——出走。
他去了英国,原因一模一样:不堪忍受惩罚性的财富税和遗产税。
这些创造了瑞典经济奇迹的基石型企业家,是解决了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就业的。
他们本该是国家的英雄。但在那套“均贫富”的税收逻辑下,他们创造的财富越多,反而成了越大的“罪人”,成了被优先“打土豪”的对象。
他们除了出走,别无选择。
如果说,宜家和利乐的故事,已经是几十年前的“旧伤疤”,那我们来看一点新鲜的,正在发生的“大出血”。
这次的主角,是挪威。对,就是那个靠着北海石油,富得流油,常年霸占人类发展指数榜首的国家。
从2022年开始,挪威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富豪出逃潮”。
几十位亿万富翁和成百上千的千万富翁,拖家带口,打包资产,集体“跳船”,目的地出奇地一致——瑞士。
领头人之一,是挪威最富有的工业家之一,谢尔·英奇·勒克。
他在2022年9月,高调宣布将自己的居住地迁往瑞士的卢加诺。
为什么?导火索是挪威的“财富税”。
这个财富税,堪称是“发动机冷却器”里的终极武器。
它不管你的资产是能下金蛋的母鸡(比如盈利公司的股票),还是仅仅是看起来值钱的石头(比如暂时无法变现的资产),它每年都要在你全部净资产的头上,固定刮走一层皮(大约1%)。
勒克算了一笔账,他每年需要缴纳的财富税,远远超过他从公司获得的分红。
这意味着什么?他为了给国家交税,每年都必须卖掉一部分公司的股票。
他的公司,这个能为挪威提供就业、创造价值的经济实体,正在因为税收的原因,被他自己一点一点地“吃掉”。
这是一种制度性的自残。
勒克的出走,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据统计,仅在2022年,离开挪威的超级富豪们,就带走了总计超过6000亿挪威克朗(约合4000亿人民币)的财富。
这笔钱,本可以用来在挪威投资、建厂、研发、创造就业。
但现在,它们都流向了瑞士。 挪威政府本想用财富税这把小刀,在富人身上多割点肉,分给穷人。
结果,这把刀太锋利了,富人直接带着整个身家跑了。
现在,政府不仅一分钱财富税都收不到了,连他们未来可能贡献的所有所得税、消费税,也都成了泡影。
这正是“漏水的桶”最悲惨的结局:不但水漏光了,连桶都给你端走了。
人才和资本的外流,不仅仅发生在“老钱”和实业家身上。
在新经济领域,这套僵化的体系同样在扼杀创新。
我们来看瑞典的另一个骄傲,全球最大的流媒体音乐平台,声田(Spotify)。
2016年,Spotify的两位创始人,丹尼尔·埃克和马丁·洛伦松,联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
这不是一封感谢信,而是一封“最后通牒”。
他们警告瑞典政府,如果再不改革,他们将被迫把公司未来的发展重心和数千个高薪工作岗位,转移出瑞典。
他们的抱怨是什么?
除了高昂的个人所得税让吸引全球顶尖工程师变得困难重重之外,更致命的,是两点:
第一,斯德哥尔摩严重的住房短缺。这是政府过度管制市场的必然结果。
第二,也是最关键的,是瑞典对“员工股票期权”征收的惩罚性税收。
在美国硅谷,用股票期权来吸引和激励核心员工,是科技公司成功的标配。公司初期没钱,就给大家发期权,许诺一个共同富裕的未来。
这是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但在瑞典,员工获得股票期权的税负,远高于其他国家。
这使得Spotify根本无法和谷歌、苹果这样的美国巨头,在人才市场上进行公平竞争。
政府想用高税收来保障“公平”,结果却砍断了新兴企业赖以生存的“激励链条”。
虽然Spotify最终没有完全搬走,但这次公开的抗议,已经撕开了北欧模式温情脉脉的面纱。
整个北欧,绝大部分优秀的IT人才,都跑去了英国和美国。
这个道理太简单了,他有能力年入百万美元,在北欧要交六十万的税,在美国只需要交十五万,你说他走不走?
越优秀的人,越能够进行跨国迁徙。
丹麦,这个童话王国,也面临着自己的税收童话破灭的窘境。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可以称之为“临时富人”和“科技旋转门”。
我们先看一个标志性人物:拉斯马斯·勒多夫。
这个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创造的东西,支撑了今天互联网世界的半壁江山——PHP编程语言。
勒多夫是丹麦裔的程序员,但他职业生涯的辉煌时期,以及PHP语言的发扬光大,主要都在哪里?美国和加拿大。
为什么?原因很简单。
在丹麦,一个顶尖程序员的收入,可能超过60%要用来缴税。这意味着,你每写一行价值100块钱的代码,到手的可能不到40块。
而这40块,还要面对全球最高的消费税(25%)之一。
更重要的是,丹麦不仅对收入征重税,对资本利得,比如你创业成功后出售公司股权的收益,同样毫不手软。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 你打工,大部分钱被拿走;你创业,成功后更大一部分钱被拿走。
对于勒多夫这样拥有创造世界级产品潜力的人来说,留在丹麦,就等于接受一个“财富天花板”。
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对自己才华和努力的一种制度性折价。所以,他选择了“用脚投票”。
这个选择,在丹麦的科技和金融圈里,已经成为一种心照不宣的惯例。
许多有抱负的丹麦年轻人,他们的职业规划是这样的:在丹麦接受免费的优质教育,大学毕业后,在国内积累一些初步经验。
一旦羽翼渐丰,或者有一个好的创业点子,立刻奔赴伦敦、柏林、苏黎世或者硅谷。
他们在国外奋斗十年、二十年,实现财富积累。
等到想退休,或者子女需要享受福利的时候,再考虑回到丹麦。 他们就像候鸟一样,在创造价值的黄金年龄,飞离了丹麦这片高税收的土地;而在需要消耗福利的年龄,又可能飞回来。
丹麦的税制,无形中鼓励了一种“人才旋转门”效应:培养人才,然后目送他们离开去创造财富,最后可能还要迎接他们回来消耗财富。
这笔账怎么算,都是亏的。
芬兰的情况则更为特殊。 在诺基亚这个巨无霸倒下后,芬兰迫切需要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大批从诺基亚出走的工程师,催生了蓬勃的游戏产业,比如创造了《愤怒的小鸟》的Rovio和《部落冲突》的Supercell。 这本该是芬兰经济的“第二春”。但高税收再一次扮演了“拦路虎”的角色。
我们来看Supercell这家公司。
它在2013年被日本软银收购,后来又被腾讯控股。为什么这家芬兰的明星公司,其股权结构会变得如此“国际化”?
除了商业上的考量,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芬兰的税制。
对于创始人来说,将公司做到如此巨大的体量,如果想在芬兰本土进行资本运作或者传承,将面临天文数字的税收。将公司出售给外国巨头,一次性完成纳税,然后个人移居海外,成了一个更“划算”的选择。
Supercell的创始人之一伊尔卡·帕纳宁,虽然至今仍是芬兰的纳税大户和商界领袖,但他和他的同行们,常年都在为芬兰的税制环境奔走疾呼。他们认为,高昂的资本利得税和缺乏吸引力的员工期权税收政策,正在让芬兰的游戏产业“为他人做嫁衣”。
具体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
尽管芬兰是全球人均产出游戏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根据芬兰游戏产业报告,大部分收入(超过95%)都来自海外市场。
这很正常。
但不正常的是,大量游戏公司的创始人和核心高管,选择将居住地和个人财富管理中心,设在瑞士、新加坡甚至阿联酋等地。
他们的人可能还在赫尔辛基的办公室工作,但他们的“财富之根”,已经悄悄地移植到了海外。
这是一种更隐蔽的人才与资本的“双重流失”。
芬兰的土地上,诞生了创新的想法和产品,但最终沉淀下来的财富,却大量地绕开了本国的税收系统。
瑞典的问题,则更深刻地体现在对“专家”的惩罚上。
我们都听过“一万小时定律”,说的是任何领域的专家,都需要经过约一万小时的锤炼。这背后是巨大的时间、精力和机会成本的投入。
一个顶尖的外科医生、一个资深的金融分析师、一个经验丰富的律师,他们的高收入,是对这“一万小时”投入的回报。
但在瑞典的超高累进税制下,这个回报被严重压缩了。
根据瑞典经济学家马格努斯·亨雷克森等人的研究,瑞典是发达国家中,大学教育回报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比一个高中毕业生,在一生中多赚的钱,在税后计算,差距非常小。
当一个外科医生辛苦一辈子,最后发现自己的税后终生收入,和一个早早参加工作、享受各种福利的普通工人相比,并没有拉开本质差距时,他的心理会如何变化?
跑嘛!
留下的人怎么活?整个社会出现了躺平文化。
对于那些留下来的人,高税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他们的心态。既然冒尖要挨打,那我就不冒尖了。
我干一份朝九晚五、安安稳稳、不出错的工作就行了。那种拼一把,单车变摩托的创业激情,在这种环境里,是很难生长出来的。
所以,高税收,从经济上看,它不仅仅是个抽水机,它还是个发动机冷却器,甚至是个刹车片。
它系统性地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和创新活力。
这里,我们必须提到那个著名的巴斯夏的破窗谬论。
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说,一个小男孩打破了面包店的窗户。
有人说,这是好事啊!你看,玻璃店老板有生意了,他赚了钱,又会去买别的东西,这就促进了经济循环。
巴斯夏说,你们都错了。
你们只看到了看得见的 —— 玻璃店老板赚了钱。但你们没有看到看不见的 —— 如果窗户没破,面包店老板本来打算用这笔钱,去给自己买一套新衣服。那么,服装店老板的生意就来了。
窗户破了,只是把财富从服装店老板那里,转移到了玻璃店老板那里。但社会总财富,还净损失了一扇窗户的价值。
这个道理,完美地适用于我们对税收的评价。
我们看得见的,是政府用税收建起来的、雄伟的图书馆、漂亮的歌剧院、宽敞的医院。我们会为这些公共成就而赞叹。
但我们看不见的是什么?
是那笔钱如果留在老百姓手里,他们会用来干什么。
可能张三会用这笔钱,开一家小小的咖啡馆,雇佣两个人。
可能李四会用这笔钱,送他的孩子去学钢琴。
可能王五会把这笔钱,投资给一个有前途的科技创业公司。
这无数个被扼杀在摇篮里的、分散的、民间的消费和投资,就是我们看不见的代价。
政府项目,因为是集中的、有形的,所以特别容易被我们看到和称赞。而市场的自发创造,因为是分散的、零星的,所以我们常常忽略。
这就造成了一个巨大的认知偏差:我们总是高估了税收带来的好处,而严重低估了它造成的损害。
第三个层次:心理上的变化
如果说,税收在伦理上是可疑的,在经济上是低效的,那么它在心理和文化层面,则像一种慢性毒药,慢慢地改变一个社会的气质。
这种改变,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它把创造者变成了算计者。
当税收制度变得极其复杂和沉重时,社会上最聪明的一群人,他们的精力会投向哪里?
不是去研发新技术,不是去开拓新市场,而是去研究税法。
如何合理避税、如何利用政策漏洞、如何进行税务筹划,成了一门显学。最顶尖的会计师、律师,赚得盆满钵满。企业家们,花在和税务顾问开会上的时间,可能比花在和工程师开会上的时间还多。
整个社会的智力资源,就这么被大量地内耗在如何与税收系统博弈这件不创造任何价值的事情上。
一个国家的精英,从价值创造者的角色,慢慢蜕变成了规则算计者的角色。
这方面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我们上一章提到的,瑞典国宝级的童话作家,阿斯特丽德 · 林格伦(《长袜子皮皮》的作者)的故事。
1976 年,她惊讶地发现,自己当年的边际税率,竟然高达 102% !也就是说,她每多赚 100 克朗,不仅要全交上去,还得自己再倒贴 2 克朗。
这简直是荒谬的笑话。
于是,这位童话大师,写了一篇新的童话,叫《波佩里波萨在莫尼斯马尼亚》。
讲一个女巫,在一个遥远的国度,被课以重税的故事。
这篇充满讽刺的童话,在瑞典社会引起了轩然大波,甚至被认为是导致当年社会民主党下台的原因之一。
一个连国宝级作家都要花心思去研究税法、写文章来抗议的国家,它的商业环境和社会风气,已经扭曲到了什么程度?
第二,它模糊了个人的和国家的之间的界限,催生了依赖文化。
在一个低税收的社会,产权边界是清晰的。
我辛苦赚来的钱,就是我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人们会珍惜自己的财富,并为自己的生活负责。
但在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这个边界变得模糊了。
人们的心态会变成:反正我赚的钱,一多半都要交上去。那我为什么不从这个庞大的 ‘ 公共池子 ’ 里,想办法多捞一点回来呢?
于是,如何合法地(甚至不那么合法地)占有公共福利,就成了很多人的生活重心。
身体没病?想办法开个病假条,在家领病假工资。
还能工作?想办法提前退休,领养老金。
想装修房子?看看政府有没有什么节能补贴、环保补贴可以申请。
个人对个人的直接责任感,变成了个人对一个抽象的系统的索取权。
那种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自立精神,慢慢被国家应该为我的人生负责的依赖精神所取代。
这是一种非常深刻的国民性侵蚀。它把一个充满活力的、由无数个负责任的个体组成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消极的、由无数个等待被喂养的巨婴组成的社会。
好了,我们今天用三把刀,把税收这个东西,从里到外解剖了一遍。
我们发现:
在伦理上 ,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财产转移,其自愿和契约的外衣,经不起推敲。
在经济上,它像一部财富粉碎机,通过制造无谓损失、惩罚成功、扼杀创新,系统性地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活力。
在心理上,它像一种慢性毒药,把国民从创造者引向算计者,从自立者引向依赖者。
所以,北欧模式那一切问题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原罪上——对私有财产的过度侵犯。
那个从摇篮到坟墓的承诺,听起来很美,但它的首付款,就是你个人经济自由和财产权利的大部分。
而它的分期付款,则是整个社会活力的缓慢衰退。
北欧国家之所以还能维持,我们反复强调,是因为它们在实施这套制度之前,已经积累了太多的财富和太强的工作伦理文化。
它们就像一个身体底子极好的壮汉,在进行一场长期的、缓慢的放血疗法。他现在看着还行,但总有一天,血会流干的。
羡慕北欧人人收入一样的人,不过是渴望通过国家这个手,强行抢走他人的财产,来为自己的消费买单。
但他们没有想到,别人是长了脚的,越有才能的人,脚更灵活,更会出走,你这么搞,那老子不在这里玩了行不行?
这么简单的道理,居然在北欧几国没有几个人懂?可见,人类的愚蠢是不可想象的。
那么,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用这笔天量的税款,还干了什么呢?它不光提供福利,还深度介入了另一个关键领域 —— 劳动力市场。
它与强大的工会联手,号称要保护工人。
但这种保护,是真的保护吗?它又保护了谁,排斥了谁?
在下一篇,我们将走进北欧那个看似和谐,实则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我们会看到,那扇为圈内人提供过度保护的大门,是如何把无数年轻人和外来者,冷酷地关在门外的。
这又是一个看得见的温暖,和看不见的残酷的故事。
|
|
||||
相关文章